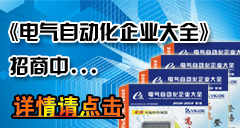中國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可為現代企業管理體系所用?我個人覺得有(you)三(san)個方面:
其一,傳統文化(以國學為代表)為自然生長出來的創業家構建自己的自圓其說的價值體系提供銓釋邏輯,由于中國人的信仰中高度關注命運之學,而我們的傳統文化又多為強調個人修為以“避壞命尋好運”的人為之學,這就使得以人事為本的傳統文化得到了著力點;
其二,中國政治文化的重目標、重計劃而建立的績效衡量模式與倒逼(先定目標再給自己找壓力)機制為企業管理中的目標化與高(gao)球(qiu)化自我施壓(ya)機制提供了參考。
其三,中國流行文化的開放性與短周期導致了對于許多新鮮元素的興趣與接納能力,并具備對各類異質元素的消化與重構能力,而這恰恰是“中間之國”的文化特性——化萬國之精巧而為我用,這使得我們的管理文化強調開放學習而(er)又不斷(duan)革(ge)新。
在改革開放中走出來的企業家,不少是自然、湊巧或天才地吸納了這些文化肥力,但也甚少有人在自覺的意義上系統地加以梳理。但是中國文化不(bu)只是有其(qi)(qi)肥(fei)力,也有其(qi)(qi)垃圾性的(de)一(yi)面,其(qi)(qi)不(bu)良之(zh����i)面突出(chu)地表(biao)現(xian)在三個方面:
其一是過于以中國為中心,缺乏其他文化角度的見識,缺乏對于非中國事物的廣泛了解與融匯,尤其以傳統文脈為訴求者往往形成文化優越感(其實中國今日的明清文脈也不必然就代表了中國的整體傳統),從而限制了自己具備對本土與他國文化平衡熔煉的能力。
其二是政治文化的目標性也導致行動取向的單一性與功利性,對其他人與其他方面的元素了解與體諒較少,因此行動往往過于具有侵略性與不擇手段性,在管理表現(xian)上往往就是“野蠻生長”,這在產(chan)業低端化的時(shi)候(hou)尚可(ke)勉強可(ke)行(xing),而在高(gao)端及更為(wei)全球化的行(xing)動半(b�������an)徑下(xia)更不(bu)可������(ke)行(xing)了。
其三,流行文化的無根現象使得企業可持續性受到嚴重挑戰,這種無根現象既表現了缺少核心思想家及對于流行文化現象的深度解讀和把握能力,也缺少在管理上對于培養、建造員工想像力的新空間,跟風或者盲目的時髦管理詞匯較多。
中國文化是很歷史的,歷史有啟發性,但歷史不太提供實際的解決方案。朝向未來的前瞻模式與未來思考是有價值的。我非常欣賞馮侖先生在他的歷史化模式的暢銷書《野蠻生長》之后,有意寫一本中華民族與另一民族在未來的一場交戰中的互相改變之作,有這樣的開始、想像甚至魔幻之作,也不失為企業家及企業管理研究者思維取向的一種改變。